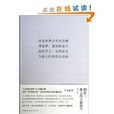《三联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专题作品,资深主笔李伟为了接近真实的胡适,从安徽到北京到美国到台湾,顺着胡适的命运轨迹,通过採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以清晰流畅的笔调细緻地描述了大师的一生。五十年前,他与时代格格不入,五十年后,中国再次与他相遇。
基本介绍
- 书名: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
- 类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3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9787511334701
- 作者:李伟
-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 页数:182页
- 开本:32
- 定价:32.00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百年文化名人”专题作品
作者简介
李伟,知名媒体人,《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出生于1978年,北京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2000年入职《三联生活周刊》。出版作品有《超越者》。
专业推荐
媒体推荐
历史回顾是《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专题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採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发现新信息,辩驳已有的结论,回顾之目的是为寻求它新的认识意义。——《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
名人推荐
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简直找不到第二个。”——李敖
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熊培云
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熊培云
图书目录
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时代的前夜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反孔子的“托拉斯”
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
“正义的火气”
“杀君马者道旁儿”
主义向左,问题向右
“不合时宜”的歧路
忍不住的新努力
自由主义的观象台
“好人当政”与“跪着造反”
“最不名誉的事”
“悖主”与“善后”
“掉下来”的导师
批评者的跌宕起伏
“被革命压死了”
“胡适系反党”
北大中兴
“憎恨残暴也憎恨虚妄”
守卫课桌
杂誌与救国
“民治”与“新式独裁”
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
北大校长
十年计画
没有选择的选择
民主的“装饰品”
“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
“过河卒子”
晚年胡适:美国、中国台湾与蒋介石
胡蒋之间
不做大哥
对胡适的“围剿”
自由主义之路
被四面夹击的胡适
胡适之死
胡适的“非典型性”
秩序与共识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
“被杀死的摩西”
时代的前夜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反孔子的“托拉斯”
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
“正义的火气”
“杀君马者道旁儿”
主义向左,问题向右
“不合时宜”的歧路
忍不住的新努力
自由主义的观象台
“好人当政”与“跪着造反”
“最不名誉的事”
“悖主”与“善后”
“掉下来”的导师
批评者的跌宕起伏
“被革命压死了”
“胡适系反党”
北大中兴
“憎恨残暴也憎恨虚妄”
守卫课桌
杂誌与救国
“民治”与“新式独裁”
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
北大校长
十年计画
没有选择的选择
民主的“装饰品”
“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
“过河卒子”
晚年胡适:美国、中国台湾与蒋介石
胡蒋之间
不做大哥
对胡适的“围剿”
自由主义之路
被四面夹击的胡适
胡适之死
胡适的“非典型性”
秩序与共识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
“被杀死的摩西”
序言
序一
2012年年初,北京《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李伟先生与我联繫,表示希望出版一期有关“胡适与自由主义”的专号。他还专程来台访问,让我谈谈胡适先生晚年的种种,又派了一位摄影记者到胡适纪念馆拍了许多照片。后来这一期专号在该年5月的周刊上发表,甚获好评。最近他又将专号的稿子整理、扩充,要出版一本有关胡适的专书,我很为他高兴,谨以此文敬表祝贺之意。
身为“20世纪中国思想第一人”或“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的胡适是一个永恆的话题。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他与鲁迅齐名,是海峡两岸各自推戴的“文化英雄”。胡适的一生涉及了中国政治、学术的各个领域,凡是讨论近代中国的议题,大概都绕不过胡适。目前书店中有关胡适的书不少,一类是胡适先生自己的作品,如《四十自述》《胡适文存》《胡适文集》,或唐德刚先生为他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等;另一类则是他人所写的有关胡适生平与思想的专书,如李敖的《胡适评传》、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罗志田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与江勇振的近作《捨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等。此外,有关胡适研究的名家还有耿云志、欧阳哲生、周质平、章清、邵健等教授。
李伟先生的这一本书与上述两类的作品都不相同。他细读了胡适先生的“夫子自道”,又吸收学术界许多严谨的论着,再以清晰流畅的笔调细緻地描述了大师的一生。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这不但因为胡适生平涉及的人物、事件错综複杂,对他的评估分歧很大;另一个原因是胡适的思想与许多作为都是超越时代的,眼光不够敏锐者往往看不清楚。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倒是看得很清楚,在举国上下以数百万字来大力批胡之际,毛主席曾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的确,胡适先生的成就与限制,要经过历史的积累、沉澱,到21世纪时才看得清楚。
这样一来,现在的确是书写胡适、“替他恢复名誉”的好时机。21世纪,人们所看到的胡适应该较能超脱时代的泥淖。几个月以前我去日本东京访问,有一天在旅馆的《产经新闻》上看到一篇报导。这是2012年10月9日该报《远响近声》时事专栏作者千野境子因有感于钓鱼台事件之争端,所写的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现在日本需要一个胡适》(《いま日本に胡适がほしい》)。作者感叹当前日本外交界没有人才,找不到一个像胡适一样能在国际上以有说服力的方式与高明的手腕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解决此一国际争议。众所周知,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做了百余场演讲,其中1942年3月23日在华盛顿的演讲《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尤其能够打动国际视听,将抗战模拟于西方文明之中“专制与民主的对垒”,让世人了解“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临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作者认为此一宣传方式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取得了“道义的优位性”。抗战期间中国能够取得许多国际援助(如各种贷款)与胡适在外交方面的努力有直接的关係。很可惜后来他与宋子文不和,又反对蒋夫人访美,1942年辞去了驻美大使一职。
胡适除了在外交上杰出的作为受到肯定,最让日本人佩服的是胡适对中日战局与太平洋战争的预测。千野氏提到胡适提出的“日本切腹而中国介错”的理论(见《胡适日记》1935.6.27中抄录他写给王世杰的一封信)。“介错”一词是和製汉语,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它的意思。日本武士切腹时必须请他最好的朋友从背后砍其头,才能迅速地完成切腹这一壮举,从背后砍下切腹者人头之人即被称为“介错人”。这一句话是指日本全民族走上了切腹自杀的道路,中国人必须以“最好的朋友”来做他们的“介错人”(胡适曾研究过日本的切腹,他根据《吕氏春秋》指出此举源于中国,见《胡适日记》1930.3.7)。他呼吁日本人必须认清此一影响中日两国命运之悲剧。不过胡适也感叹地说,国人必须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咬定牙根”準备苦战,不然“中国还不配做他们的‘介错人’”。后来局势的发展,也确如胡适所述,由中日对垒走向国际战局。
胡适先生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1949年之后在台湾的表现,担负起李敖所谓启蒙之“播种者”的角色。这一部分在本书中《晚年胡适:美国、中国台湾与蒋介石》一章的访谈中有所介绍。他与蒋介石之间是“道不同而相为谋”,很能反映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威权体制、强人政治之下,如何相忍为国。其实,胡适所面对的挑战不但来自蒋介石,还受到其他保守者,如张其昀、徐复观、徐子明等人之抨击,同时他与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之间也有矛盾。这一处境就是书中所说的“被四面夹击的胡适”。胡适在当时思想光谱上可谓一个温和而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他毕生“一以贯之地”坚持自由、民主之价值,并希望能在取得政府信任的前提下来批评政府。对他来说,过度支持现实政权、肯定传统,或过度激烈地抨击时政、追求西化,都不恰当。这一点使他与吴国桢、雷震、殷海光等激烈地批判政治,甚至不惜以身相殉的做法很不相同。孰是孰非,值得深思。
最近有很多人提到“民国范儿”的说法,民国史上的确有不少风骨嶙峋的人格典範值得我们追念怀想。读者如果仔细地阅读李伟先生的这一本书,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和我有类似的感受,觉得将胡适誉为“民国范儿”,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序二
《胡适与自由主义》是李伟独立完成的《三联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第二个,第一个是他在2011年完成的《鲁迅之疑》。
历史回顾是《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专题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採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发现新信息,辩驳已有的结论,回顾之目的是寻求它新的认识意义。《三联生活周刊》及时反映现实热点的封面专题,一般都由三五人彼此协作,在短时间内赶製。而这类不需要时间逼迫、独特而具深思空间的长线选题,也鼓励希望建立自己独特研究方向的主笔独立去探索,并给予其足够的时间空间及採访成本支持。李伟的《鲁迅》与《胡适》,都属于这样的实践成果。
其实,在新世纪到来之初,我们便有了做“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想法——对上一个世纪的眺望与重新关注,对这个世纪新的道路选择能否有坐标性的意义?我们以为,从文化人物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民族百年所走过的血泪沧桑,有可能比政治人物更能脱离标籤化与简单的意识形态判断,更有可能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态複杂机理,去辨析一些悲剧产生之根源。而这些人物的命运,也许更能深入折射出这百年历史进程中一些能发人深思的问题,以致我们在这一个百年,能少付出那些本不该付出的代价。
选题总是要靠足以胜任的人的自我希求与自我奋斗来完成,我总是说,“有什幺人,才有什幺样的选题”。这个系列得以实现,这开头两个人物所完成的质量,完全依赖于李伟对历史追问的原动力与他为此付出的辛苦与努力——从广泛阅读,寻找出问题,到出发去现场寻找当年的氛围,通过採访接近那些已经尘封的真相,再审慎地给出殚精竭虑后自己的分析。从準备到採访再到成文,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是一个研究课题的深入过程。这样的选题实施,编辑部付出的是採访成本——首先,给以两三个月,允许他能不被干扰地深入研究领域;然后,提供採访费用,支持他去接近历史现场。当然,这些仅是外部支持,能否拿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只能靠本人的投入与作为。这种投入应该有些理想主义,实用主义者一般不会不惜成本,去花那幺多的气力。
李伟这两年,在鲁迅与胡适这两个人物上所作的努力,我以为是寻找到了一种极有价值的途径。为接近鲁迅,他从绍兴到日本到上海、南京、北京;为接近胡适,他从安徽到北京到美国到台湾,基本都顺着他们命运的轨迹,边走边思考。因为鲁迅在先,胡适在后,胡适也就比鲁迅更具体地提出了问题、讨论了问题,更显成熟。他依靠了许多学人已经建立的坐标,但他自己在这些坐标基础上的追问,也可喜地超越了自己学识的局限。就胡适道路而言,从新文化运动激情洋溢的旗手,到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希望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维持个人学术与思考的自由独立,又无法将个人剥离于社会环境。既要学术独立,所有学术又都离不开它与社会现实的急切关係;既要反抗专制,追求独立人格,又必须穿梭于各种政要之间,无法离开被四方夹击的中心舞台。“从左派到中间偏左、中间偏右,再到右派”,其实一天也无法独立自由,只能被政治现实裹挟在中间。
我一直觉得,一个重要的媒体,不应该只关心即时信息的意义;一个有作为的主笔,也不应将自己等同于追逐即时信息传播的小记者。一个重要的媒体的使命,应该是调动它的优质人力资源,为他们提供一个个足以伸展各自敏感触觉的小空间,激励他们的理想主义,鼓励他们成为深入的研究者与探索者,再将这些探究成果传达奉献给读者。在信息传播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其实会有越来越多对这种投入足够成本的独家深入信息的需求——当廉价信息铺天盖地时,有质量的信息会越来越显其价值的,毕竟,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会仅满足于一知半解。而这正应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们所要去努力追求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有更多这样的课题,提供更多这样辛勤获得的沉甸甸的成果。它们可以是历史,但给出的应该是对现实思考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能少生产些信息垃圾,多给社会提供些可供留存的印迹了。
2012年年初,北京《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李伟先生与我联繫,表示希望出版一期有关“胡适与自由主义”的专号。他还专程来台访问,让我谈谈胡适先生晚年的种种,又派了一位摄影记者到胡适纪念馆拍了许多照片。后来这一期专号在该年5月的周刊上发表,甚获好评。最近他又将专号的稿子整理、扩充,要出版一本有关胡适的专书,我很为他高兴,谨以此文敬表祝贺之意。
身为“20世纪中国思想第一人”或“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的胡适是一个永恆的话题。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他与鲁迅齐名,是海峡两岸各自推戴的“文化英雄”。胡适的一生涉及了中国政治、学术的各个领域,凡是讨论近代中国的议题,大概都绕不过胡适。目前书店中有关胡适的书不少,一类是胡适先生自己的作品,如《四十自述》《胡适文存》《胡适文集》,或唐德刚先生为他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等;另一类则是他人所写的有关胡适生平与思想的专书,如李敖的《胡适评传》、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罗志田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与江勇振的近作《捨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等。此外,有关胡适研究的名家还有耿云志、欧阳哲生、周质平、章清、邵健等教授。
李伟先生的这一本书与上述两类的作品都不相同。他细读了胡适先生的“夫子自道”,又吸收学术界许多严谨的论着,再以清晰流畅的笔调细緻地描述了大师的一生。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这不但因为胡适生平涉及的人物、事件错综複杂,对他的评估分歧很大;另一个原因是胡适的思想与许多作为都是超越时代的,眼光不够敏锐者往往看不清楚。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倒是看得很清楚,在举国上下以数百万字来大力批胡之际,毛主席曾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的确,胡适先生的成就与限制,要经过历史的积累、沉澱,到21世纪时才看得清楚。
这样一来,现在的确是书写胡适、“替他恢复名誉”的好时机。21世纪,人们所看到的胡适应该较能超脱时代的泥淖。几个月以前我去日本东京访问,有一天在旅馆的《产经新闻》上看到一篇报导。这是2012年10月9日该报《远响近声》时事专栏作者千野境子因有感于钓鱼台事件之争端,所写的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现在日本需要一个胡适》(《いま日本に胡适がほしい》)。作者感叹当前日本外交界没有人才,找不到一个像胡适一样能在国际上以有说服力的方式与高明的手腕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解决此一国际争议。众所周知,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做了百余场演讲,其中1942年3月23日在华盛顿的演讲《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尤其能够打动国际视听,将抗战模拟于西方文明之中“专制与民主的对垒”,让世人了解“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临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作者认为此一宣传方式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取得了“道义的优位性”。抗战期间中国能够取得许多国际援助(如各种贷款)与胡适在外交方面的努力有直接的关係。很可惜后来他与宋子文不和,又反对蒋夫人访美,1942年辞去了驻美大使一职。
胡适除了在外交上杰出的作为受到肯定,最让日本人佩服的是胡适对中日战局与太平洋战争的预测。千野氏提到胡适提出的“日本切腹而中国介错”的理论(见《胡适日记》1935.6.27中抄录他写给王世杰的一封信)。“介错”一词是和製汉语,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它的意思。日本武士切腹时必须请他最好的朋友从背后砍其头,才能迅速地完成切腹这一壮举,从背后砍下切腹者人头之人即被称为“介错人”。这一句话是指日本全民族走上了切腹自杀的道路,中国人必须以“最好的朋友”来做他们的“介错人”(胡适曾研究过日本的切腹,他根据《吕氏春秋》指出此举源于中国,见《胡适日记》1930.3.7)。他呼吁日本人必须认清此一影响中日两国命运之悲剧。不过胡适也感叹地说,国人必须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咬定牙根”準备苦战,不然“中国还不配做他们的‘介错人’”。后来局势的发展,也确如胡适所述,由中日对垒走向国际战局。
胡适先生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1949年之后在台湾的表现,担负起李敖所谓启蒙之“播种者”的角色。这一部分在本书中《晚年胡适:美国、中国台湾与蒋介石》一章的访谈中有所介绍。他与蒋介石之间是“道不同而相为谋”,很能反映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威权体制、强人政治之下,如何相忍为国。其实,胡适所面对的挑战不但来自蒋介石,还受到其他保守者,如张其昀、徐复观、徐子明等人之抨击,同时他与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之间也有矛盾。这一处境就是书中所说的“被四面夹击的胡适”。胡适在当时思想光谱上可谓一个温和而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他毕生“一以贯之地”坚持自由、民主之价值,并希望能在取得政府信任的前提下来批评政府。对他来说,过度支持现实政权、肯定传统,或过度激烈地抨击时政、追求西化,都不恰当。这一点使他与吴国桢、雷震、殷海光等激烈地批判政治,甚至不惜以身相殉的做法很不相同。孰是孰非,值得深思。
最近有很多人提到“民国范儿”的说法,民国史上的确有不少风骨嶙峋的人格典範值得我们追念怀想。读者如果仔细地阅读李伟先生的这一本书,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和我有类似的感受,觉得将胡适誉为“民国范儿”,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序二
《胡适与自由主义》是李伟独立完成的《三联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第二个,第一个是他在2011年完成的《鲁迅之疑》。
历史回顾是《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专题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採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发现新信息,辩驳已有的结论,回顾之目的是寻求它新的认识意义。《三联生活周刊》及时反映现实热点的封面专题,一般都由三五人彼此协作,在短时间内赶製。而这类不需要时间逼迫、独特而具深思空间的长线选题,也鼓励希望建立自己独特研究方向的主笔独立去探索,并给予其足够的时间空间及採访成本支持。李伟的《鲁迅》与《胡适》,都属于这样的实践成果。
其实,在新世纪到来之初,我们便有了做“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想法——对上一个世纪的眺望与重新关注,对这个世纪新的道路选择能否有坐标性的意义?我们以为,从文化人物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民族百年所走过的血泪沧桑,有可能比政治人物更能脱离标籤化与简单的意识形态判断,更有可能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态複杂机理,去辨析一些悲剧产生之根源。而这些人物的命运,也许更能深入折射出这百年历史进程中一些能发人深思的问题,以致我们在这一个百年,能少付出那些本不该付出的代价。
选题总是要靠足以胜任的人的自我希求与自我奋斗来完成,我总是说,“有什幺人,才有什幺样的选题”。这个系列得以实现,这开头两个人物所完成的质量,完全依赖于李伟对历史追问的原动力与他为此付出的辛苦与努力——从广泛阅读,寻找出问题,到出发去现场寻找当年的氛围,通过採访接近那些已经尘封的真相,再审慎地给出殚精竭虑后自己的分析。从準备到採访再到成文,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是一个研究课题的深入过程。这样的选题实施,编辑部付出的是採访成本——首先,给以两三个月,允许他能不被干扰地深入研究领域;然后,提供採访费用,支持他去接近历史现场。当然,这些仅是外部支持,能否拿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只能靠本人的投入与作为。这种投入应该有些理想主义,实用主义者一般不会不惜成本,去花那幺多的气力。
李伟这两年,在鲁迅与胡适这两个人物上所作的努力,我以为是寻找到了一种极有价值的途径。为接近鲁迅,他从绍兴到日本到上海、南京、北京;为接近胡适,他从安徽到北京到美国到台湾,基本都顺着他们命运的轨迹,边走边思考。因为鲁迅在先,胡适在后,胡适也就比鲁迅更具体地提出了问题、讨论了问题,更显成熟。他依靠了许多学人已经建立的坐标,但他自己在这些坐标基础上的追问,也可喜地超越了自己学识的局限。就胡适道路而言,从新文化运动激情洋溢的旗手,到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希望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维持个人学术与思考的自由独立,又无法将个人剥离于社会环境。既要学术独立,所有学术又都离不开它与社会现实的急切关係;既要反抗专制,追求独立人格,又必须穿梭于各种政要之间,无法离开被四方夹击的中心舞台。“从左派到中间偏左、中间偏右,再到右派”,其实一天也无法独立自由,只能被政治现实裹挟在中间。
我一直觉得,一个重要的媒体,不应该只关心即时信息的意义;一个有作为的主笔,也不应将自己等同于追逐即时信息传播的小记者。一个重要的媒体的使命,应该是调动它的优质人力资源,为他们提供一个个足以伸展各自敏感触觉的小空间,激励他们的理想主义,鼓励他们成为深入的研究者与探索者,再将这些探究成果传达奉献给读者。在信息传播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其实会有越来越多对这种投入足够成本的独家深入信息的需求——当廉价信息铺天盖地时,有质量的信息会越来越显其价值的,毕竟,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会仅满足于一知半解。而这正应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们所要去努力追求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有更多这样的课题,提供更多这样辛勤获得的沉甸甸的成果。它们可以是历史,但给出的应该是对现实思考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能少生产些信息垃圾,多给社会提供些可供留存的印迹了。